音乐与戏剧的结合,诞生了音乐剧,它是一种比歌剧更加贴合普通大众的舞台艺术形式。千禧年之后,中国内地开始越来越多地引入西方音乐剧。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奥地利、德国、俄罗斯等国的音乐剧纷至沓来,给中国演出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在聆听音乐剧中激动人心的歌曲时,在观赏音乐剧美轮美奂的舞台和灯光时,你有没有想过它们是怎么制作的?音乐剧中的歌曲与普通的流行歌曲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百老汇、伦敦西区的音乐剧能成为业界标杆?为什么有的剧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却亏损严重?为什么《剧院魅影》能长演不衰……
3月29日,《一听就懂的音乐剧》读者见面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资深音乐剧人、《一听就懂的音乐剧》的作者费元洪,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音乐剧研究者慕羽在畅谈中分享音乐剧的艺术特色、国际经验与中国发展路径。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北京舞蹈学院学生表演经典音乐剧选段,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活动现场
三联书店编辑黄新萍介绍说,《一听就懂的音乐剧》源自83期同名音频课程,“国内资深音乐剧人费元洪在书中,讲述了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的音乐剧代表作,既有老牌经典《剧院魅影》,也有潮流新作《汉密尔顿》,既有成功制作,亦不乏失败的案例。既有创作背景、音乐构思、舞美设计、文化内涵,也有商业模式、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总结。无论是音乐剧小白,还是音乐剧从业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和信息。”
针对“中国何时能产出经典音乐剧”的疑问,两位嘉宾均表示需要时间沉淀。费元洪认为,只要保持创作活力,经典自然会水到渠成;慕羽则强调要平衡商业与艺术,“当下最重要的是培养健康的行业生态。”

活动海报
“90后、00后的年轻观众已经成为消费主力”
费元洪的音乐剧之路,起自2002年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悲惨世界》,他作为中文字幕的翻译入行。现而今圈内人称“费老”的费元洪,彼时还在音乐学院读研究生,课余时间喜欢看戏写剧评。“当年舞台演出的字幕都是人工手打出来的,作为字幕员的我就坐在剧场一个昏暗的小角落。”
“其实打字幕是件很专业的事。《悲惨世界》是宗教性与人性交织的史诗,中文版翻译需平衡信息量与观剧体验。一开始我恨不得把剧本里所有的内容都翻译出来,导演却说有闻必录会非常影响观众的观感。正面是舞台,侧面是字幕条,如果两三秒就换一屏,观众的头会一直跟着在转,搞得像养鸡场一样。所以主次要分清楚,字幕是次,舞台表演是主。所以字幕内容一定要精简,做到七八秒换一次才是合适的。”
谈及音乐剧与歌剧的区别,费元洪认为后者以管弦乐、美声唱法为主,采用的是古典音乐语言;前者则更通俗化,含纳了电声乐和流行唱法。在叙事方式上,歌剧偏重艺术性表达,音乐剧更注重故事性和娱乐性。“但两者的本质上都是用音乐讲故事。音乐剧融合表演、舞美、灯光等元素,是综合的视听艺术。核心在于听觉体验,书名《一听就懂的音乐剧》就是为了强调音乐的重要性。”
说到西方音乐剧的特色,费元洪如数家珍:英美音乐剧,百老汇商业性强,如《西区故事》舞蹈叙事突出;韦伯的《剧院魅影》成功融合摇滚与古典,作为伦敦西区的产业标杆,推动了音乐剧全球化;法国音乐剧旋律自由、情感浓烈,强调音乐性,戏剧结构隐于氛围中;德、奥音乐剧如《莫扎特》《伊丽莎白》凸显了民族特性,哲理性强、结构严谨;俄罗斯音乐剧旋律民族化,但产业尚不成熟,如《奥涅金》多改编自经典文学。

费元洪
“音乐剧是一颗种子,在不同土壤中长出不同的样子。”费元洪认为音乐剧并无所谓“正宗”,不同国家的音乐剧风格各异。《巴黎圣母院》《伊丽莎白》之所以历来在中国广受欢迎,因其旋律性、悲剧性与东方写意、留白的审美相契合。百老汇的《汉密尔顿》(2015)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则在于嘻哈音乐与历史题材的反差感,“打破精英叙事,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平权表达。”
现任职上海文化广场的费元洪,多年来带领团队主办与承办上海国际音乐剧论坛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对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发展洞若观火,“文化自信是比较出来的——法国人敢走自己的路,德国人敢走自己的路,中国人也敢。我们从早期‘仰视西方’到逐步建立自信,现而今90后、00后的年轻观众已经成为消费主力。上海汉口路上的亚洲大厦已经成了‘魔都百老汇’,主打沉浸式小剧场,挤满了下班后的年轻人。国风音乐剧如《大状王》受欢迎,也证明了东方审美的市场潜力。”
《蜘蛛侠》《金刚》等大制作的失败,警示“砸钱堆特效”观众并不买账,内容远比炫技更重要,应该回归戏剧的情感内核;中文版西方音乐剧《妈妈咪呀》商业表现不佳,也表明亟需发展本土故事。“中国音乐剧需要在全球化中保持自信,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未来我们应融合国际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剧体系。”费元洪认为可以学习德、奥的结构设计,如昆策的“覆水难收”的戏剧节点,再结合中国叙事传统。“中文语言四声调的特性导致字幕的必要性,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传统戏曲里自报家门、虚拟动作等的写意表达。”
“年轻观众是行业未来,他们的审美需求将推动原创剧目的发展。而产业繁荣肯定需要‘量’的积累,不必苛求单一经典,多元探索才更有生命力。”面对当下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带来的影响,费元洪表示,“剧场是‘一群人演给一群人看’的手工业,科技再发达,也替代不了真实的共情。真人表演的现场感永远无法被技术完全替代。”
“音乐剧的在地化必须尊重本土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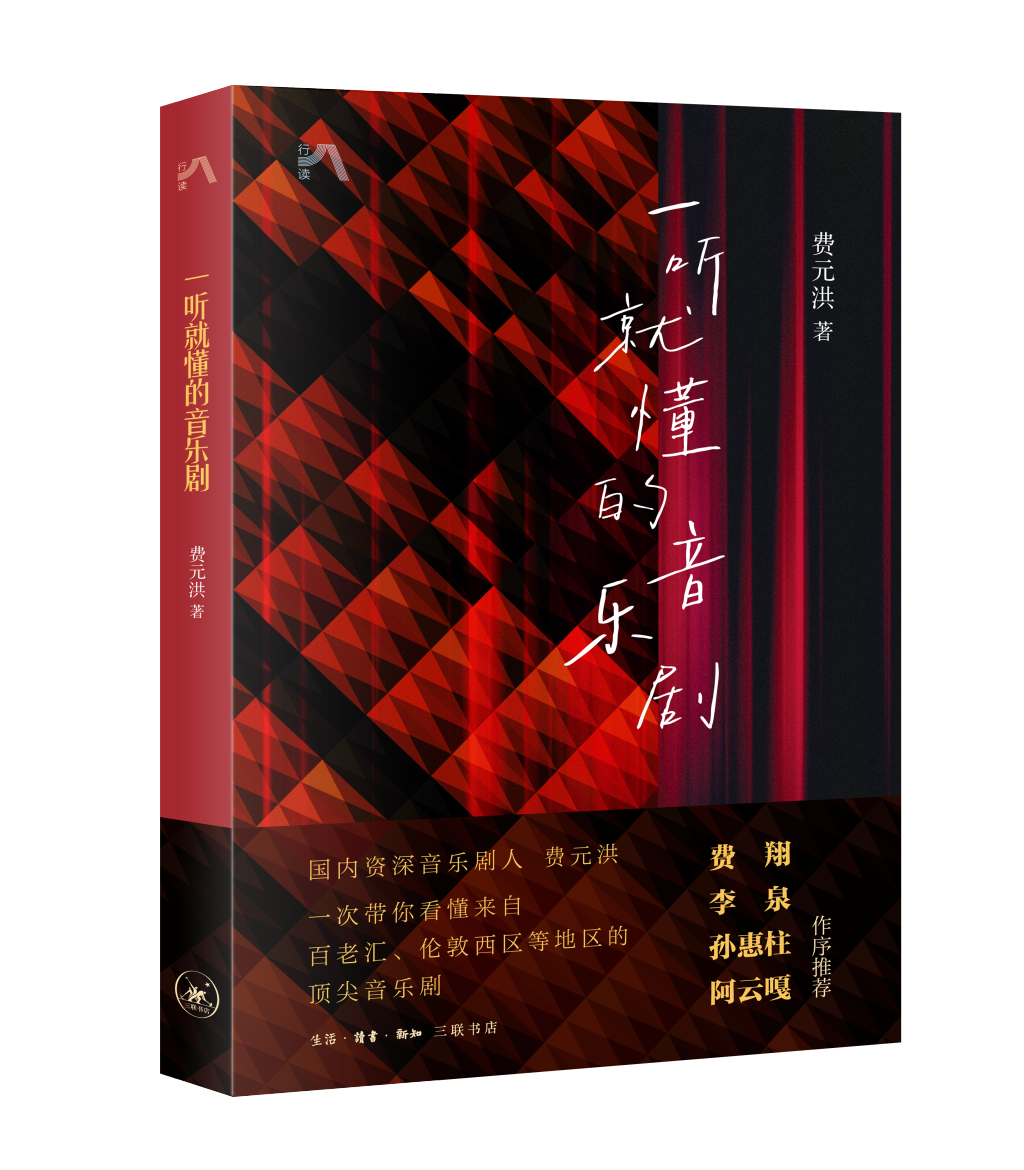
《一听就懂的音乐剧》书影
1987年,随着引进百老汇经典音乐剧《乐器推销员》(中文版)和《异想天开》(中文版),音乐剧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慕羽从学术角度,分析了西方音乐剧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在她看来,音乐剧分为叙事音乐剧(Book Musicals)、点唱机音乐剧(Jukebox Musicals)、概念音乐剧(Concept Musicals)以及从头唱到尾的音乐剧(Through-Sung)。
“中国观众易于接受强调故事完整性,如《西区故事》这样的叙事音乐剧。而像《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这样从头唱到尾的音乐剧,音乐全程主导叙事,对旋律要求极高,中文版就会面临语言适配的挑战。”慕羽特别指出:“分类不是枷锁,而是工具箱。关键是要找到最适合中国故事的表达方式,可能是这些类别的混合体,也可能是全新的类型。”
早期观众对西方音乐剧存在“仰视”心理,如今市场虽逐渐成熟,但文化隔阂仍旧存在。慕羽以《魔法坏女巫》在中国的遇冷为例,说明了本土化改编的重要性,“音乐剧的在地化必须尊重本土审美,而非简单复制西方模式。”
“我们的观众也在从‘学习西方’转向‘多元选择’。中国音乐剧需要找到自己的叙事方式,而非简单模仿百老汇或西区。”对于原创音乐剧,慕羽特别肯定国风音乐剧和方言作品的探索,同样提到粤语音乐剧《大状王》的市场成功,证明本土文化表达的潜力。同时,她也提醒行业应警惕“快餐式创作”,在商业化浪潮中还是要坚守艺术品质。
“舞蹈不是装饰,而是角色的第二语言——它必须回答‘你在跳什么?’”以《西区故事》《芝加哥》为例,舞蹈从“华丽的表演”发展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关键手段。从自身专业出发,慕羽谈了舞蹈在音乐剧中的角色。
她引用美国舞蹈设计家杰罗姆·罗宾斯的观点,强调“舞蹈必须推动叙事”,需要与角色情景深度结合,而非炫技型的单纯娱乐。“罗宾斯首创‘编舞导演’这一角色,确立了舞蹈段落必须经得起删减测试——若去掉不影响剧情,就是失败的’这一行业标准。我们的原创音乐剧也可以学习这种戏剧性编舞的思维。”
谈及当下国内的音乐剧教育与行业生态,慕羽介绍说年轻一代如00后,通过《声入人心》等节目接触音乐剧,行业需要关注新观众的需求。而中国音乐剧演员从“无戏可演”到如今供不应求,也反映了市场的增长。
“但这背后也有隐忧,对比话剧的经典化路径,国产原创音乐剧至今尚未出现‘时代标杆’。我们必须以历史眼光来看待艺术沉淀,关注幕后耕耘者和老一辈音乐剧人,要‘热爱’与‘耐心’并重。市场真正繁荣与否,取决于观众是否愿意为‘戏剧的本质’买单,而非明星或特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