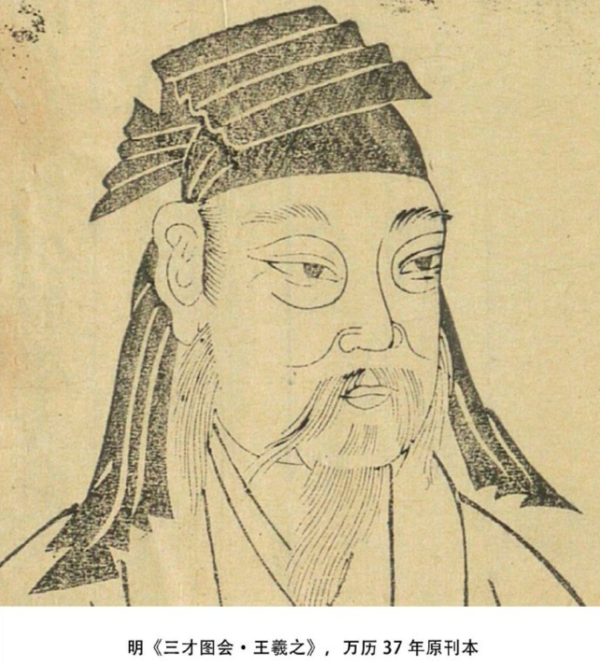
王羲之画像
轻学术近年来在国内成了一股潮流。所谓的轻学术,就是既注重可读趣味,又不失学术深度。和纯粹的普及性读物相比,轻学术依然没有放弃引领读者思考的可能性。《王羲之》可以称得上是轻学术的典范。在吉川忠夫反复强调大概、或许以及可能的同时,他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则:结论需要材料。为什么“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只能够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合理的推测。这个简单的道理却很容易被读者忽视,在不少读者的眼中,历史学家应该是知识渊博而无所不知的。虽然王羲之被尊为书圣,但是流传下来与他相关的史料并不很多,因而就需要用别的可靠材料来补充。吉川忠夫在1971年所写的后记中指出,这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充分利用了王羲之的尺牍”。尺牍就是书信,可是那时候的书信非常简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时候要靠“推理和想象”才能够被脑补尺牍所写内容的场景。这样的坦白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也让读者更加接近学术的“真相”——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既有材料的推理和想象,就如同必然会有虚构色彩的电影一样。时至今日,不少学者还会标榜自己所告诉读者的是“真实”的,相比之下,吉川忠夫的坦率“或许”才更真实。
用电影的角度来看,各种王羲之的逸事像是正常的情节推进,而他的尺牍则如同个人的内心独白,我们需要细细品味,才能推理出其中所展现的另一个王羲之。吉川忠夫把尺牍中的王羲之“想象”成一个关心他人而心地善良的人。这与《世说新语》中傲气满满的王羲之形象的确有所不同。他还从王羲之的尺牍中找到了“目前”二字,认为这是理解王羲之的关键所在。在吉川忠夫看来,王羲之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找寻到了“目前”之乐,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珍惜当下。“目前”让王羲之成为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似乎他是一个快乐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则蕴藏着难以磨灭的不安感。不管怎样,吉川忠夫笔下的王羲之都带着主角的光环,他对王羲之几乎没有做任何的负面评价。也许,他把评价的权利交给了读者。
四、剧末的“彩蛋”
把《王羲之》看成一部电影,就不能够有太多的剧透。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从中找到吉川忠夫为我们准备的台阶,一步一步地接近我们想要看到的王羲之。可是,不管我们的口味有何不同,《王羲之》的中译本在客观上为所有的中国读者准备了一个彩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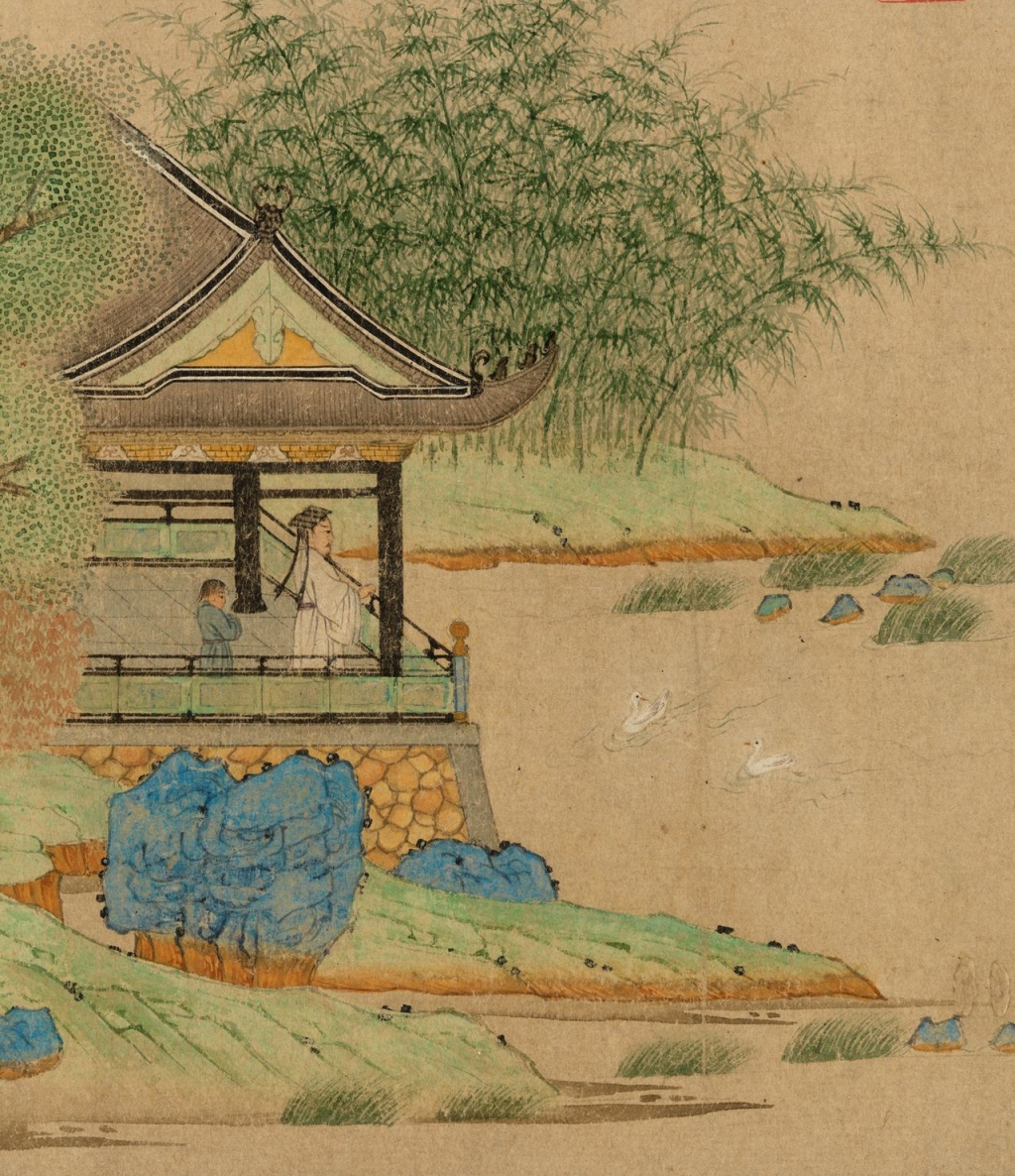
王羲之观鹅图,元钱选绘。
《王羲之》最初的目标读者是四十年前的日本读者。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好地理解王羲之的方方面面,吉川忠夫在不少地方提到了相应的日本和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份意外的收获。我们原本想看看日本学者如何解读王羲之,结果顺带着了解了不少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可以从更多视角来重新审视王羲之。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大众读者,这种跨文化的比较都颇具启发性。这也是为何说它讲的是王羲之又不是王羲之的原因之一。在谈到王羲之的书法时,吉川忠夫用十七世纪日本著名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理论来阐释自然和人工的关系。松尾芭蕉强调诗歌应当出于自然而生之情,反对矫揉造作;吉川忠夫认为这与王羲之书法的浑然天成一脉相通。他说:“就国别、时代而言,书法、俳句并非同类。但作为艺术,两者的精神是相通的。”而在讲述王羲之所处的东晋时,他提到了日本皇室所收藏的奈良时代到日本的《丧乱帖》,并用十字军试图夺回圣地巴勒斯坦来形容东晋夺回华北的决心。这不啻为读者打开了另一扇门。有多少读者在看到此处时心中会闪过一个念头:十字军也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话题,深入地了解一下十字军东征也许也不错吧……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